解析我国《合同法》第22条与第26条:默示承诺与意愿实现的法律诠释
本作品内容为默示的承诺与意思实现——我国《合同法》第22条与第26条的解释论.doc,格式为 doc ,大小 99328 KB ,页数为 22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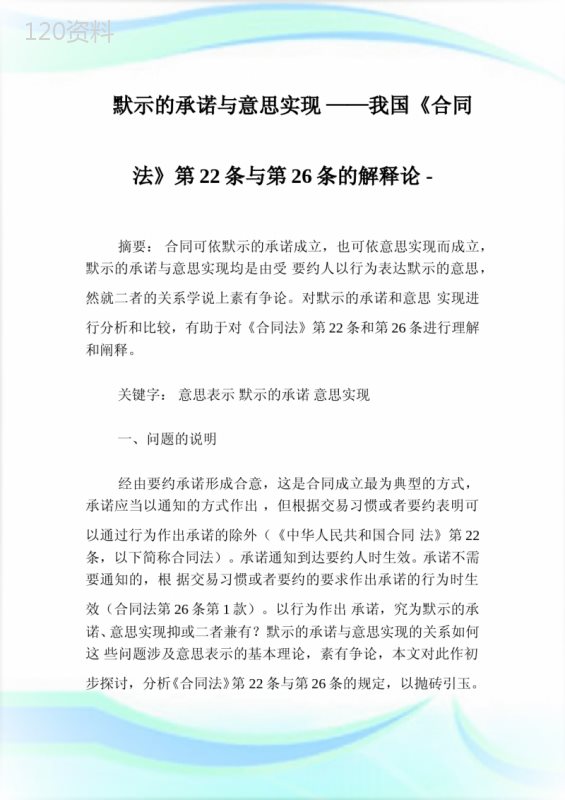
('默示的承诺与意思实现——我国《合同法》第22条与第26条的解释论-摘要:合同可依默示的承诺成立,也可依意思实现而成立,默示的承诺与意思实现均是由受要约人以行为表达默示的意思,然就二者的关系学说上素有争论。对默示的承诺和意思实现进行分析和比较,有助于对《合同法》第22条和第26条进行理解和阐释。关键字:意思表示默示的承诺意思实现一、问题的说明经由要约承诺形成合意,这是合同成立最为典型的方式,承诺应当以通知的方式作出,但根据交易习惯或者要约表明可以通过行为作出承诺的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22条,以下简称合同法)。承诺通知到达要约人时生效。承诺不需要通知的,根据交易习惯或者要约的要求作出承诺的行为时生效(合同法第26条第1款)。以行为作出承诺,究为默示的承诺、意思实现抑或二者兼有?默示的承诺与意思实现的关系如何这些问题涉及意思表示的基本理论,素有争论,本文对此作初步探讨,分析《合同法》第22条与第26条的规定,以抛砖引玉。二、意思表示的方式、默示的承诺与意思实现(一)意思表示的方式意思表示可以采取明示的方式或默示的方式作出,相应地区分为明示的意思表示与默示的意思表示。[1](P74)明示的意思表示,其行为人直接将其效果意思表示于外,例如甲向乙表示愿以200万元购某屋。默示的意思表示,则由特定行为间接推知行为人的意思表示,例如在自助餐厅取面包而食之,或将汽车停于收费的停车场。于此等情形,行为人虽未明言购买面包或利用停车场,但由食用面包或停车的事实,可推知其有购卖面包或利用停车场的意思。沉默或单纯的不作为,即当事人既未明示其意思,亦不能籍他项事实,推知其意思,原则上不具意思表示的价值,仅于例外场合,比如基于当事人的约定或在所谓“规范化的沉默”场合,可作为意思表示。[2](P339)默示的意思表示又称为“以可推断之行为发出的意思表示”。[3](P209)(二)默示的承诺承诺是受要约人同意要约的意思表示(合同法第21条),意思表示既可有明示与默示两种方式,自然也就会有“明示的承诺”与“默示的承诺”。[4](P176)且可以认定为依默示的意思表示进行承诺的场合,并不少见,比如按照要约的内容实际送货,或者对与要约同时送来的物品付款等,属对要约人的因承诺而成立之合同的履行行为,作出此等行为即属默示的承诺。[5](P64)依前述结论,默示的承诺可表述为以可推断之行为发出的承诺。上述结论,可以从一些立法文件中加以印证。比如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CISG)第18条第1款规定,受要约人的表示同意要约的陈述或其他行为是承诺。沉默或不作为本身并不构成承诺(重点号后加)(注:CISGart.18par.1:Astatementmadebyorotherconductoftheoffereeindicatingassenttoanofferisanacceptance.Silenceorinactivitydoesnotinitselfamounttoacceptance.为了本文用语的统一,对CISG的条文内容均未采纲中文官方译本。)。《国际商事合同通则》(PICC)第2?6条第1款的表述与之完全相同。《欧洲合同法原则》(PECL)第2:204条规定:(1)受要约人作出的任何形式的陈述或行为,一旦它表明了对要约的同意,即为承诺。(2)沉默或不作为本身并不构成承诺(重点号后加)(注:PECLart.2:204ACCEPTANCE:(1)Anyformofstatementorconductbytheoffereeisanacceptanceifitindicatesassenttotheofter.(2)Silenceorinactivitydoesnotinitselfamounttoacceptance.)。默示的承诺可作广义与狭义的区分。自广义而言,凡从特定的行为(甚至不作为)中间接地推知行为人承诺的意思表示,均属之,不论此意思表示是否需要通知要约人。自狭义上讲,默示的承诺仅限于需要将默示作出的承诺的意思表示通知要约人的情形,承诺无须通知的情形排除在外。(三)意思实现意思实现,系德语Willensbetatigung的意译,日语中亦称“意思实现”。《德国民法典》第151条(不需向要约人表示的承诺)对此作了规定,[6]“根据交易习惯,承诺无需向要约人表示,或者要约人预先声明无需表示的,即使没有向要约人表示承诺,承诺一经作出,合同即告成立。应根据要约或者当时情况可以推知的要约人的意思,来确定要约约束力消灭的时间。”依德国学者通说见解,在《德国民法典》第151条中,承诺的意思必须通过某种方式表达出来,亦即必须使该意思显示于外部,但受要约人无需针对要约人表达或显示其承诺意思,承诺意思也无需到达要约人那里。[3](P280)《德国民法典》的这一规定亦影响到《日本民法典》(注:《日本民法典》第526条(契约成立时期):(1)隔地人间的契约,于发承诺通知时成立。(2)依要约人的意思表示或交易上的习惯,不需承诺通知时,则契约于已有可认为是承诺意思表示的事实时成立。)和我国台湾“民法”(注:“台湾民法第161条(意思实现):(1)依习惯或依其事件之性质,承诺无须通知者,在相当时期内,有可认为承诺之事实时,其契约成立。(2)前项规定,于要约人要约当时,预先声明承诺无须通知者,准用之。),其相应的民法文献,称此种规定为”意思实现“。[5](P70)[7](P34)[4](P180)[8](P26)[9](P27)[10](P70)意思实现的特征在于:其一,承诺无须通知;其二,受到严格限制,要求是根据交易习惯或者根据要约人预先的声明;其三,合同自出现认定承诺意思的事实或行为时(承诺意思实现时)成立。依学者通常所举事例,比如客人用电报预订旅店房间,旅店老板将客人的姓名登记入预订客房名单,将要约人实物要约寄来的书籍签名于书页以示所有,均属依意思实现而成立合同。意思实现所表述的规则在CISG、PICC及PECL中也是可以见到的。CISG第18条第3款规定:如果根据该项要约或依照当事人之间确立的习惯作法或惯例,受要约人可以做出某种行为,例如与发运货物或支付价款有关的行为,来表示同意,而无须向要约人发出通知,则承诺于该项行为做出时生效,但该项行为必须在上一款所规定的期间内做出(注:CISGart.18par.3:However,if,byvirtueoftheofferorasaresultofpracticeswhichthepartieshaveestablishedbetweenthemselvesofofusage,theoffereemayindicateassentbyperforminganact,suchasonerelatingtothedispatchofthegoodsorpaymentoftheprice,withoutnoticetotheofferor,theacceptanceiseffectiveatthemomenttheactisperformed,providedthattheactisperformedwithintheperiodoftimelaiddownintheprecedingparagraph.)。PICC第26条第3款基本相似,规定:但是,如果根据要约本身,或依照当事人之间建立的习惯做法或依照惯例,受要约人可以通过做出某行为来表示同意,而无须向要约人发出通知,则承诺于做出该行为时生效(注:PICCart.2?6par3:However,if,byvirtueoftheofferorasaresultofpracticeswhichthepartieshaveestablishedbetweenthemselvesorofusage,theoffereemayindicateassentbyperforminganactwithoutnoticetotheofferor,theacceptanceiseffectivewhentheactisperformed.)。PECL第2:205条第3款在合同成立的时间上有所不同,规定:如果根据要约、当事人之间业已确立的习惯做法或者惯例,受要约人可以履行某种行为来对要约作出承诺而无须通知要约人,合同自开始履行该行为时成立(注:PECLart.2:205par.3:Ifbyvirtueoftheoffer,ofpracticeswhichthepartieshaveestablishedbetweenthemselves,orofausage,theoffereemayaccepttheofferbyperforminganactwithoutnoticetotheofferor,thecontractisconcludedwhentheperformanceoftheactbegins.)。“意思实现”在《合同法》之前的中国大陆立法中并没有规定,这一概念只是出现在民法著述中。[11](P382)[12](P302)[13](P42)[14](P58)《合同法》第22条肯定了承诺无需通知的情形的存在,第26条第1款规定,承诺不需要通知的,根据交易习惯或者要约的要求作出承诺的行为时生效。自此,意思实现在中国大陆立法中有了根据。就意思实现的本质,学说上颇有分歧。有的认为它并非意思表示(注:参见[日]三宅正男:《契约法(总论)》,青林书院1978年版,第25页。三宅教授认为,依意思实现之合同成立不仅是属于依要约承诺以外的方式成立合同,甚至超出了意思表示合致的框架,只是一种成立合同的便法。因此,对由此发生的合同成立及其效力,法律行为的一般理论并不当然适用,惟在有些场合可以类推适用而已。);有的认为它属于一种广义的意思表示;[9](P171)有的认为其本质仍可作为一种意思表示。[15](P11)本文认为意思实现仍然是一种意思表示,自《合同法》条文来看,使用了“承诺不需要通知”字样(第26条第1款),显然将“意思实现”亦作为一类承诺,而“承诺是受要约人同意要约的意思表示”(第21条),由此,自解释论的立场,意思实现至少在我国立法上是作为一种意思表示的。三、默示的承诺与意思实现(一)学说的分歧关于默示的承诺与意思实现,学说的分歧大别为两类:区别存在说与区别否定说。1.区别存在说。承认意思实现与默示的承诺有区别的学说中又有如下不同解释:(1)传统的理解是,承诺是一种意思表示,意思表示可分解为三项要素:效果意思、表示意思与表示行为。[16](P171)而在意思实现场合,由于不存在表示意思(想将承诺的意思向外部表示的意思),因而与意思表示不同,因意思实现的合同成立有别于意思之合致,届独立的合同成立方式。[8](P27)[17](P31)[19](P59)比如有学者认为,如果行为不是向要约人作出的,比如宾馆依要约而保留房间的行为,属于意思实现;而行为是向要约人作出的场合,比如订货的发送,属于默示的承诺。[7](P34)(2)认为表示意思并非意思表示的要素之一,[1](P73)[19](P242)[20](P191—192)[21](P211)[22](P340—358)因而,意思实现与承诺的意思表示的差异并非在于表示意思之有无;只是在对于要约人没有作出通知这一点上,与承诺的意思表示有差异。从而,根据要约的要求送货上门的行为,其中含有承诺的意思表示,不属此所谓意思实现。[5](P71)2.区别否定说。关于意思实现的法律性质,学说上有“默示的承诺说”,依照该说,意思实现与依要约承诺成立合同的方式是没有必要区别的。有的见解认为默示的承诺与意思实现乃至事实合同关系并非是截然分开的,认为在很多场合它们所指射的是同一的法律关系(注:参见[日]水本浩:《契约法》,有斐阁1995年版,第27-28页。我国学者余延满先生认为,意思实现并非一种有别于要约与承诺的合同订立方式,只不过承诺有其特殊性而已。参见其《合同法原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21页。另外,沈达明与梁仁洁先生认为,所谓默示的意思表示,是指表意人以某种行动或态度所显示的意思。学理称之为意思的证实(willenbagung)。参见其编著《德意志法上的法律行为》,对外贸易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49页。龙卫球先生亦有相似见解,认为默示的意思表示,又称“意思证明”(Willenbetaetigung),指以社会的非习用方法为表达,他人根据具体情况才可推知表达外观意思的情形。参见其著《民法总论》,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第508页。)。(二)前提界定在讨论默示的承诺与意思实现的关系时,首先应对使用的概念作出界定(参照示意图).如果是使用广义上的默示的承诺,则无疑意思实现也应当列入其中。如果使用狭义上的默示的承诺概念,意思实现则是有别于默示的承诺的。本文拟在狭义上使用默示的承诺概念。附图{D412N501.BMP}(三)区别的实益意思实现与默示的承诺二者区别的意义在于,以发送订购物品为例,应认为默示的意思表示,必须于物品送达要约人时,合同始告成立。其发送之事实虽已实现而未到达,不能发生承诺之效力。反之,意思实现则以客观上有可认为承诺之事实存在为必要,有此事实,合同即为成立(注:参见孙森焱:《新版民法债编总论》上册,台湾自版1999年版,第29页。对CISG第18条第3款的分析,亦有相似结论。参见沈达明、冯大同编著:《国际贸易法新论》,法律出版社1989年版,第61页。)。在前者场合,在合同成立前,不生价金风险问题;在后者场合,则有价金风险问题,如无特别约定,依《合同法》第145条,标的物交付给第一承运人后,风险由买受人承担。四、承诺的行为与承诺的通知承诺的意思可以通过行为来表示,这也正是默示的承诺与意思实现共通的地方,也由此而产生了对两者关系的模糊认识。一种认识是将意思实现理解为默示的承诺;另外,则是对于二者的关系不作深究,泛泛而谈,并出现不加区分地混用的现象。(一)意思表示的成立与生效承诺是一种意思表示,意思表示亦有成立与生效之别。意思表示的要素,虽有争论,但学者大多持“二要素说”,即仅要求具备效果意思与表示行为。效果意思之中,一是须有基础效果意思,同时要有受法律上拘束的意思。表示行为是将效果意思客观外化的过程,表示行为既可以是将表意人内心的意思书写在纸上,或用话语表达出来,也可以通过其他行为表示出来。意思表示具备效果意思和表示行为时,即为成立。成立后的意思表示是否生效,尚应当区别意思表示的类型而定。一类意思表示是需要受领的,在未经受领前,并不生效,要约、承诺、行使合同解除权之类意思表示,原则上属于此类(参见《合同法》第16条、第26条、第96条),在我国法上,受领生效就体现为“到达主义”规则。另外一类意思表示无需受领,原则上一经成立,即为生效,[20](P192)比如抛开动产所有权的意思表示。(二)承诺的通知承诺应当以通知的方式作出(《合同法》第22条前段),承诺的通知扮演什么角色呢?承诺一经具备效果意思(承诺意思)及表示行为(比如书写后装入信封),即为成立,惟此时尚不生效,因为它是一种需要经过受领才能生效的意思表示。因此,通知(notice)便发挥了传达信息的功能。由此可见,承诺的通知本身并非承诺之意思表示成立的一个构成部分,而是承诺生效的一个要件。承诺通知原则上要求在承诺期限内到达要约人。承诺通知在性质上当属观念的通知或意思的通知,属于准法律行为(注:法律关于意思表示及法律行为的规定,在如何范围内可以类推适用,应视具体行为的性质加以确定。),只要能将承诺的意思传达到,就可以。至于承诺的通知采取什么形式,法律不作要求,因而是自由的,且非须由受要约人亲自作出,比如以实际发货的方式表达承诺的意思,承运人将货物到达的信息通知要约人,只要该通知是在承诺期限内作出的,也可以发生承诺通知的效果。通知专门向要约人发出固不待论,以广告的方式向不特定人发出,只要可得预期要约人会看到该广告,也是可以的。比如甲自其同事处获悉乙有兴趣购入并转售甲的商品,甲便主动以向乙发货(现物要约),乙以在甲阅读的商业报纸上刊出出售该商品的广告的方式承诺,甲在她阅读到此则广告的时候知悉对方的承诺。[23]按照“到达主义”规则,报纸送到要约人处时合同成立。(三)承诺的行为与承诺的通知承诺通知适用于明示的承诺场合,对此不存在疑问,问题是承诺通知是否以明示的承诺场合为限?有的学者作这样的解释,[8](P27)其实这种理解并不妥当。在默示的承诺场合,承诺的意思表示是从受要约人的行为中推断出来的,对于默示的承诺,法律并不禁止,以行为承诺,大致可区分为二类:一是根据交易习惯或者要约表明可以通过行为作出承诺;二是除此之外的由受要约人自主选择作出的通过行为作出承诺。在前者场合,依法律规定,无须通知(《合同法》第22条)。而对于后者在《合同法》中既未列入例外的范围,自然要受“承诺须经通知”原则的拘束。而对于后一种情形,易为人忽略.其实,从PECL第2:205条第2款的规定中,可以有鲜明的反映,即“在以行为表示承诺之场合,合同自有关该行为的通知到达要约人时成立。”(注:PECLart.2:205par.2:Inthecaseofacceptancebyconduct,thecontractisconcludedwhennoticeoftheconductreachestheofferor.)默示的承诺场合,承诺的通知大致可区分为两种类型,一种类型是承诺的行为直接向要约人作出,此时承诺的行为与承诺的通知集合为一体。比如,要约人发信表示愿以某价格购买受要约人的某产品,受要约人未作明示承诺直接送货上门(注:值得注意的是,如果要约中表明要求受要约人直接发货,则受要约人发货的行为应当解释为因意思实现成立合同。)。另一种类型是承诺的行为并非直接向要约人作出,则需要受要约人另作承诺通知。比如,要约人要求购买受要约人的某种产品,由受要约人送货给某第三人,此时,仅有送货上门的行为,尚不能发生承诺的效力,只有在将关于送货上门的信息传达给要约人时(到达主义),合同才算是成立。当然,在后者场合,受要约人的通知既可以行为前作出(表示“我方将送货给既定第三人”),也可以在行为后作出(表示“我方已将货物送给既定第三人”)。承诺以通知要约人为原则,系承诺须经受领原则使然,并为要约人的利益而存在,但并非没有例外,于若干场合亦可发生承诺无须通知的情形。其一是要约人放弃其承诺通知利益,声明承诺无须通知,以求简便;其二是依交易习惯,承诺无须通知。于诸此例外场合,通常是自可得认有承诺的事实时起,承诺生效,合同成立。这便是所谓“意思实现”。由此可见,默示的承诺与意思实现的区别:默示的承诺需要作承诺的通知,合同自承诺的通知到达要约人时成立;而意思实现则无须作承诺的通知,合同自承诺的意思实现时成立。五、对《合同法》第22条与第26条的解释(一)合同成立的时点《合同法》第22条前段“承诺应当以通知的方式作出”,其中的“承诺”宜解释为兼指明示的承诺与默示的承诺,后段“但根据交易习惯或者要约表明可以通过行为作出承诺的除外”,是关于以意思实现方式成立合同的规定。《合同法》第26条第1款前段是承诺生效的“到达主义”规则,不分口头承诺与非口头承诺。后段是对依意思实现成立合同场合承诺生效时间的特别规定。这样,在《合同法》中,同时存在默示的承诺与意思实现两种不同的合同成立方式。二者区分的意义在于合同成立时间的判断标准不同。设若6月1日买受人乙将如下字样送到了出卖人甲:“请速发下列货物:(货物的描述).”6月2日甲向乙发送货物。6月3日上午,甲向秘书口述书信一封,拟告知乙货物已在运输途中;下午,在甲将信投邮之前,乙打电话给甲,称:“不要再发送6月1日所订货物。”甲答复称其取消订单为时已晚,因为货物已经发出。甲的信件于6月8日送达乙,货物在6月20日到达。乙以不存在合同为由,拒绝受领货物。[24]从乙的要约中要求“速发”,可以反映出来允许甲以行为承诺,合同因作出承诺的行为(发货)而成立,无须另行通知(发信),更无须要求通知的到达。另外,依《合同法》第19条第2项,乙的要约也应当属于不得撤销的。(二)意思实现的构成要件1.根据交易习惯或者要约的要求承诺不需要通知。合同因意思实现而成立,不必通知,对当事人的利益而言至关重要,故须限于特别情事,依《合同法》第26条第1款的规定,其情形有二:其一为根据交易习惯,承诺不需要通知,例如宾馆房间内冰箱中的饮料或食品,客人可以自由取出消费,最后统一结算。其二为根据要约的要求,承诺不需要通知,例如甲要求乙绘制风景油画五幅,表明将于某日上门取货。2.受要约人作出可以认有承诺意思的行为。所谓“作出承诺的行为”,实即作出可以反映承诺意思的行为,大别为两类:履行行为与受领行为。此所谓履行行为,即受要约人有履行其合同义务的行为,比如前例中乙按要约要求绘制油画的行为;所谓受领行为,即受要约人行使合同权利的行为,比如前例中宾馆客人消费冰箱中饮料或食品的行为,又如拆阅现物要约寄来的杂志的行为。单纯的沉默,除非当事人之间有特别的约定或者符合交易习惯,否则,是不可以作为“作出承诺的行为”的。即使要约中表示如果不作出承诺与否的通知,即视为承诺,受要约人也是没有作出承诺与否的通知的义务的,在不为通知之场合,合同并不成立。[8](P27)(三)意思实现与承诺行为人真实意思在依意思实现方式缔约场合,应否考虑作出承诺行为人的真实意思呢?比如寄送试阅杂志以后,继续寄送的杂志不再盖有试阅字样,收受人误认为试阅,开封阅读,合同是否成立?一类见解认为,意思实现以客观上有可认为承诺之事实存在为必要,有此事实,合同即为成立。至于承诺人是否认识该事实行为为承诺之意思表示,主观上是否有承诺之意思,在所不问,例如使用要约人送到之物品,虽主观上无为承诺而成立合同的意思,应认为合同成立。且不得以错误为由撤销其意思表示,因为意思实现不以主观上有承诺的认识为要件。[9](P29)另有见解认为,承诺之事实,应以有承诺意思为必要,此就“承诺”的本质而言,应属当然,否则意思将成为事实行为了;相对人主观上无承诺意思,仅依客观上可认为承诺之事实,即可成立合同,使其负担合同上的义务,与私法自治原则似有违背,而且不足以保护相对人利益,此在现物要约最为显然;又相对人为限制行为能力人,无行为能力人或无意思能力人时,是否能仅依客观上可认为承诺的事实,即可成立合同,亦有疑问。提出所谓可认为承诺之事实,应解为系承诺的意思依一定的事实而实现之,不必通知要约人,系承诺意思表示须经受领,始生效力之例外,学说称为“无须受领的意思表示”。真正的问题不在于承诺意思是否必要,而是承诺意思有暇疵或欠缺承诺意思时,究应如何处理。主张意思实现亦应当如同意思表示一样处理。合同虽然成立,仍可以错误为由主张撤销。[4](P182)上述两类见解,各有所据。个人以为,以采后一见解为当。如前所述,默示的承诺与意思实现分别属于须受领的意思表示与无须受领的意思表示,二者的差异在于意思表示的生效是否以通知为必要,而在具备“承诺意思”这一点上,二者当属相同。这样,意思实现亦应当作为意思表示加以处理。依传统见解误拆现物寄来的杂志,由于没有表示意思,故不成立意思表示(承诺),进而不成立合同。依现代的有力说,表示意识并非意思表示的要素,仍可依行为认定承诺,惟合同可以错误为由主张撤销。这样,再辅以合同撤销场合的信赖利益赔偿制度,能够较好地解决问题。六、结论1.默示的承诺与意思实现均可成立合同,然二者并不相同。《合同法》第22条后段及第26条第1款后段系关于意思实现的规定。关于默示的承诺《合同法》虽然没有直接规定,宜理解为《合同法》没有特别区分明示的承诺与默示的承诺而异其规则,有关承诺的一般规则,对二者均有适用。2.默示的承诺属于须经受领的意思表示,作出“承诺的行为”只是默示的承诺的成立,如欲发生承诺的效力,还须关于该“承诺的行为”的通知到达要约人。意思实现则属于无须受领的意思表示,是承诺须经受领原则的例外情形,故于“承诺的行为”作出时生效,合同成立,无须另行作出承诺的通知,亦非于承诺的通知到达时生效。3.意思实现是对承诺须经通知原则的例外,由于承诺无须通知,合同成立的具体时点并不为要约人确切掌握,对之不利,故应当严格限定其适用条件,须根据交易习惯或者要约的要求承诺不需要通知,且受要约人作出了可以认有承诺意思的行为。4.意思实现在本质上仍属意思表示,只是例外地承诺无须通知,有关意思表示的法律规定,比如错误(重大误解)等,对于意思实现仍应适用。「参考文献」[1]陈国柱,民法学(修订本)[M].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87。[2]王泽鉴,民法总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3][德]迪特尔梅迪库斯,德国民法总论[M].邵建东,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4]王泽鉴,债法原理(一)[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5][日]我妻荣,债权各论(上卷)[M].东京:岩波书店,1954。[6]B.S.Markesinis,W.LorenzG.Dannemarrn.TheGermanLawofObligations,Vol.1,TheLawofContractsandRestilution:AComparativeIntronduction[M].ClarendonPress.Oxford,1997,57.[7][日]星野英一,民法概论IV(契约)[M].东京:良书普及会,1987。[8][日]水本浩,契约法[M].东京:有斐阁,1995。[9]孙森焱,新版民法债编总论(上册)[M].台北:自版,1999。[10]黄立,民法债编总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11]王利明,郭明瑞,吴汉东,民法新论(下册)[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12]王家福,中国民法学民法债权[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1。[13]施天涛,经济“游戏”的规定-合同法的发展与完善[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5。[14]崔建远,合同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15][日]松板佑一,民法提要(债权各论)(第五版)[M].东京:有斐阁,1993。[16][日]四宫和夫,能见善久,民法总则(第五版增补版)[M].东京:弘文堂,2000。[17]史尚宽,债法总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18][日]鸠山秀夫,增订日本债权法各论[M].东京:岩波书店,1926。[19][日]我妻荣,新订民法总则[M].东京:岩波书店,1965。[20]梁慧星,民法总论(2001版)[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21]寇志新,民法总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22]邵建东,表示意识是否意思表示的要素-德国联邦最高法院储蓄所错误担保案例判决评析[A].梁慧星。民商法论丛(第17卷)[C].香港:金桥文化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00。[23]OleLandoandttaghBealeed,PrinciplesofEuropeanContractLaw,Pratsand[M].KlawerLawⅠⅡCnternational,2000,171,Ⅲuastration1.[24]JohnOflonnold,UniformLawforinternationalSalesunderthe1980UnitednationsConvention[M].KlawerLawandTaxationPublishers,1987,185.',)
提供解析我国《合同法》第22条与第26条:默示承诺与意愿实现的法律诠释会员下载,编号:1700599218,格式为 docx,文件大小为22页,请使用软件:wps,office word 进行编辑,PPT模板中文字,图片,动画效果均可修改,PPT模板下载后图片无水印,更多精品PPT素材下载尽在某某PPT网。所有作品均是用户自行上传分享并拥有版权或使用权,仅供网友学习交流,未经上传用户书面授权,请勿作他用。若您的权利被侵害,请联系963098962@qq.com进行删除处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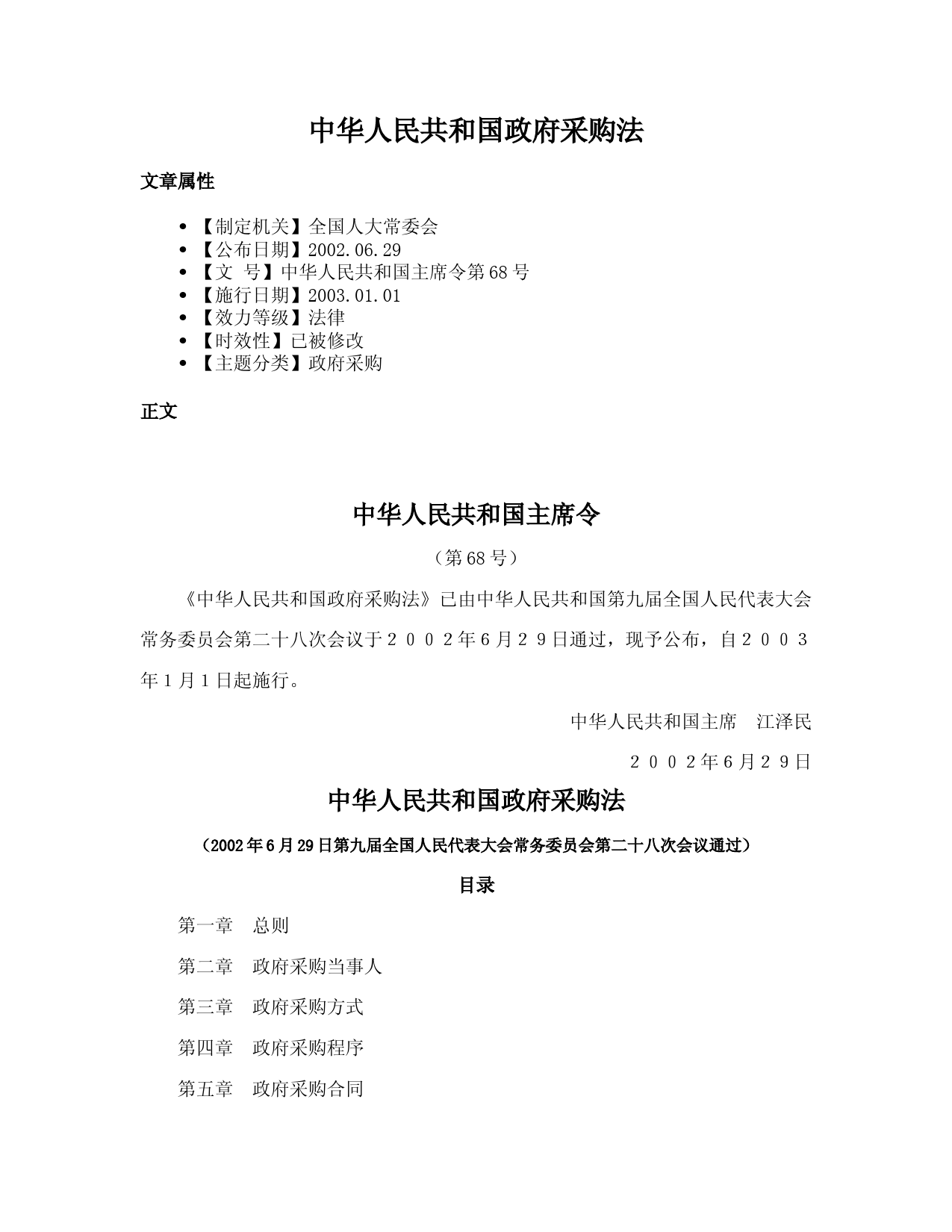 下载
下载